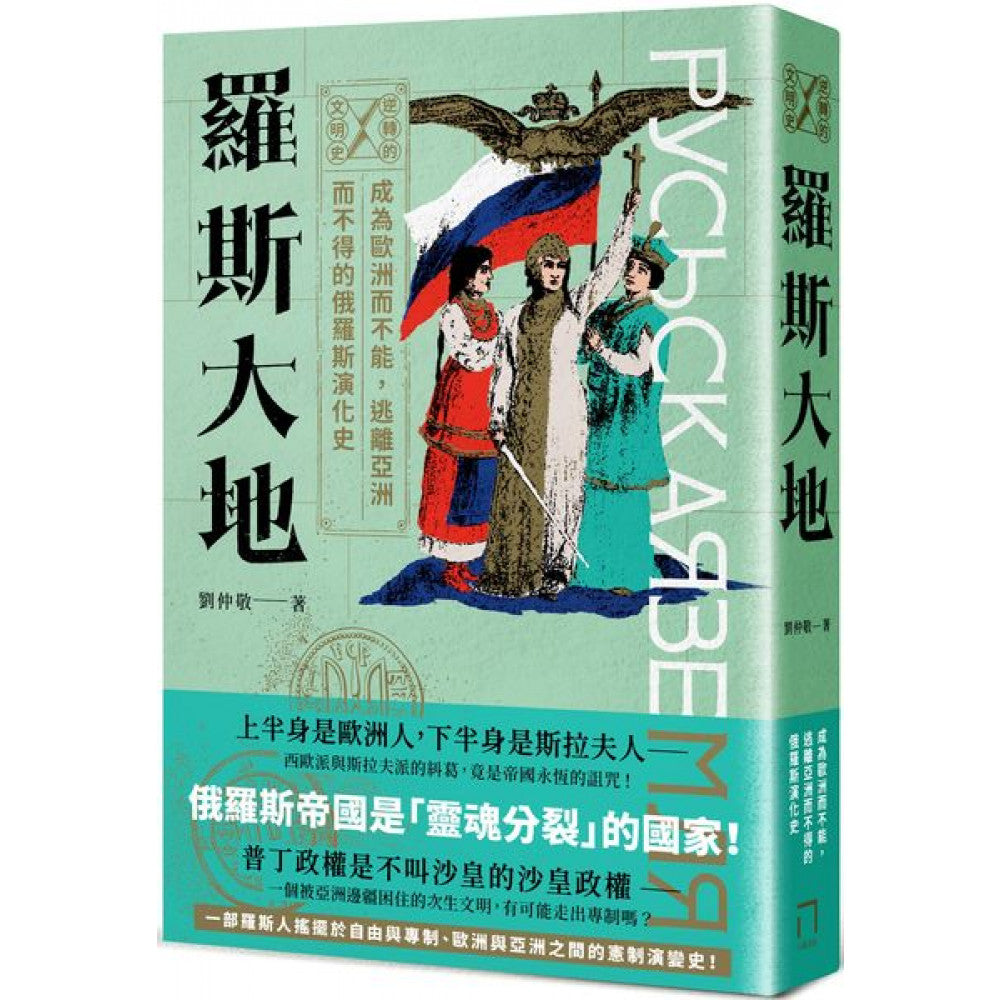1
/
of
1
八旗文化
逆转的文明史:罗斯大地──成为欧洲而不能,逃离亚洲而不得的俄罗斯演化史
逆转的文明史:罗斯大地──成为欧洲而不能,逃离亚洲而不得的俄罗斯演化史
Regular price
$46.54 SGD
Regular price
Sale price
$46.54 SGD
Unit price
/
per
Taxes included.
Couldn't load pickup availability
ISBN:9786267129838
作者:刘仲敬
出版社:八旗文化
【内容简介】
一个延伸到远东的绵延不绝的开放边疆,既是俄罗斯成为欧亚帝国的原因,同时也是它无法融入欧洲的关键。巨大的边疆、蒙古人的征服、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法统,使罗斯大地这块「次生文明」,摇摆于欧洲和亚洲之间、挣扎在自由和专制之间、被不断形成的新的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矛盾和冲突所撕裂。
而二○二二年二月发生、至今仍旧进行中的乌克兰战争,既是专制和自由、正义和邪恶的较量,也是深层和古老的文明史力量的推动。要解释俄罗斯、乌克兰、白俄罗斯这三个罗斯国家的复杂历史,以及它们和立陶宛、波兰等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文明分野,就要先回到「罗斯」这个地理概念的形成及其宪制演化的历史。
■俄罗斯一开始便携带欧洲文明的基因!而莫斯科的诞生改写了一切!
在由俄罗斯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主构成的「罗斯大地」上,古典罗斯的核心是乌克兰,即从波罗的海沿著第聂伯河往南抵达黑海这条水上商业路线。今天的乌克兰首都基辅是最古老的罗斯城邦,它的诞生是瑞典王公保护这条商业路线的结果,可以说乌克兰自古便携带欧洲文明的基因。
然而莫斯科这个边陲小邦的诞生,打破了基辅罗斯和欧洲的联系!在地理上,这归因于处在东北方向的莫斯科拥有向亚洲开放边疆拓殖的诱惑。结果,西北方向通往波罗的海的欧洲,东北方向通往亚洲大陆的边疆,就形成了罗斯世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极端类型:一种是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型,由上层贵族和商人集团控制的市民议会掌握最高权力,一种是莫斯科型,由拓殖草原森林的军役贵族所依附的大公掌握专制权力。
「诺夫哥罗德人是半个欧洲人,半个德国人,半个立陶宛人,是罗斯世界通向欧洲的纽带;而莫斯科人是半个鞑靼人,半个芬兰人,半个穆斯林,是罗斯世界通向欧亚大草原和东方各国的纽带。」这两种极端类型构成了罗斯世界的永恒母题,使它成为摇摆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灵魂分裂的国家。
■来自蒙古和拜占庭的「亚洲元素」,既是俄罗斯强大的根本,也是它最大的诅咒?
有两股来自亚洲的势力深刻影响了罗斯世界之后的演变。一股来自蒙古,一股来自拜占庭帝国(东罗马)。蒙古的征服瓦解了以基辅为主的旧罗斯世界,而莫斯科以成为蒙古代理人、又背叛蒙古的不光彩形象而崛起,成为罗斯世界的暴发户。
这也意味著罗斯世界被分成两半:依附于蒙古的、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亚洲一半,以及依附于立陶宛的、以其他商业城邦自治形式为核心的欧洲一半(相当于今天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半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、乌克兰的绝大部分)。
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流亡的东罗马公主,让莫斯科得以在政治上继承东罗马帝国的法统,以所谓的「第三罗马」自居。如果它没有继承东罗马的法统,那么莫斯科公国的地位还不如立陶宛大公国,更永远比不上跟法国和德国,然而新引入的拜占庭上层结构则使得莫斯科更加自外于欧洲。俄罗斯最大的痛苦就是永远无法成为欧洲!
■上半身是欧洲人,下半身是斯拉夫人?
西欧派(上层)VS 斯拉夫派(下层)的纠葛与对立
作为妥协而诞生的罗曼诺夫王朝,是经过混乱、分裂后的俄罗斯重新出发、全面追求欧洲化的新时代。俄罗斯跳过波兰,直接从西欧输入技术和思想。从彼得大帝到凯萨琳大帝,俄罗斯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像欧洲人;拿破仑战争以后,俄罗斯的国家威望和利益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。
然而西欧化同时强化了沙皇的专制,圣彼得堡的欧化建立在针对俄罗斯广袤内地的殖民之上。农奴制度的出现,意味著下层的东正教社会与上层的欧化阶级再度分裂。
「十九世纪的俄国自由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人认的祖先是基辅罗斯,他们要把俄罗斯人变成欧洲人。沙皇本人,至少莫斯科的沙皇,认的是拜占庭,他们要做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。而欧亚主义者认的是蒙古帝国。俄罗斯的大一统性并不来自于欧洲,甚至并不来自于拜占庭,而是来自于蒙古帝国。」
这些辩论幽灵般缠住了俄罗斯人的思考。「我到底是俄罗斯人还是欧洲人,还是两者都是」,「俄罗斯是既非欧洲、又非亚洲的一个单独的世界」。这些深层疑问,通过托尔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写作,通过自由派和三位一体专制主义者的冲突,通过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冲突,深刻地撕裂了俄罗斯社会。
■乌克兰的民族发明被苏联冻结在一九一八年,战争之火能够解冻吗?
俄罗斯帝国晚期推行的地方自治实验和陪审制,在宪制意义上是继续「成为欧洲」。在为欧洲式的立宪君主制做准备的同时,也必然产生了一系列民族发明: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乔治亚、乌克兰、白罗斯等。
但是,一战的出现和布尔什维克的成功逆袭,以及列宁式的极权国家出现,把这些正在展开的欧洲式民族国家发明状态一刀斩断。苏联像一个巨大的冰箱一样,把俄罗斯帝国内的各民族冻结在一九一八年。一九九○年代苏联解体后,这些被冻结的民族重新回到一九一八年之前,分别产生自己的民族国家,如白俄罗斯、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。这是普丁政权不愿承认、却没有办法抗拒的历史。
从这个角度看,乌克兰战争是三十年前苏联解体的巨轮、碾过罗斯大地后尚未消失的历史尘埃。而从整个罗斯世界的文明和宪制演变来看,俄罗斯入侵乌克兰,再一次证明莫斯科成为欧洲而不能,逃离亚洲而不得的历史困境。
本书是刘仲敬关于「文明和宪制」的系列讲稿之一,作者的切入角度非常独到,避开了一般常见的传统政治史的写法,比如热衷于描写王朝的兴衰、沙皇等宫廷上层政治人物的故事,而是逆转读者对文明的认知,从地理、社会组织结构、宪制演化的角度解读「罗斯大地」的历史和政治演变。
从文明和宪制的角度看俄罗斯,它是一种次生文明,其历史演化无法摆脱被地理牵制的宿命,而不得不变成灵魂分裂的国家。而莫斯科偏好用专制的形式,来解决其上下层阶级和东西方文化的结构性矛盾,否则就会造成地理的分裂!这种模式,似乎变成了俄罗斯的宿命,成为欧洲而不能,逃离亚洲而不得,在进退维谷中维持一个横跨欧亚的专制帝国的运作,这就是俄罗斯帝国在人类文明史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。
作者:刘仲敬
出版社:八旗文化
【内容简介】
一个延伸到远东的绵延不绝的开放边疆,既是俄罗斯成为欧亚帝国的原因,同时也是它无法融入欧洲的关键。巨大的边疆、蒙古人的征服、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法统,使罗斯大地这块「次生文明」,摇摆于欧洲和亚洲之间、挣扎在自由和专制之间、被不断形成的新的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矛盾和冲突所撕裂。
而二○二二年二月发生、至今仍旧进行中的乌克兰战争,既是专制和自由、正义和邪恶的较量,也是深层和古老的文明史力量的推动。要解释俄罗斯、乌克兰、白俄罗斯这三个罗斯国家的复杂历史,以及它们和立陶宛、波兰等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文明分野,就要先回到「罗斯」这个地理概念的形成及其宪制演化的历史。
■俄罗斯一开始便携带欧洲文明的基因!而莫斯科的诞生改写了一切!
在由俄罗斯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主构成的「罗斯大地」上,古典罗斯的核心是乌克兰,即从波罗的海沿著第聂伯河往南抵达黑海这条水上商业路线。今天的乌克兰首都基辅是最古老的罗斯城邦,它的诞生是瑞典王公保护这条商业路线的结果,可以说乌克兰自古便携带欧洲文明的基因。
然而莫斯科这个边陲小邦的诞生,打破了基辅罗斯和欧洲的联系!在地理上,这归因于处在东北方向的莫斯科拥有向亚洲开放边疆拓殖的诱惑。结果,西北方向通往波罗的海的欧洲,东北方向通往亚洲大陆的边疆,就形成了罗斯世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极端类型:一种是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型,由上层贵族和商人集团控制的市民议会掌握最高权力,一种是莫斯科型,由拓殖草原森林的军役贵族所依附的大公掌握专制权力。
「诺夫哥罗德人是半个欧洲人,半个德国人,半个立陶宛人,是罗斯世界通向欧洲的纽带;而莫斯科人是半个鞑靼人,半个芬兰人,半个穆斯林,是罗斯世界通向欧亚大草原和东方各国的纽带。」这两种极端类型构成了罗斯世界的永恒母题,使它成为摇摆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灵魂分裂的国家。
■来自蒙古和拜占庭的「亚洲元素」,既是俄罗斯强大的根本,也是它最大的诅咒?
有两股来自亚洲的势力深刻影响了罗斯世界之后的演变。一股来自蒙古,一股来自拜占庭帝国(东罗马)。蒙古的征服瓦解了以基辅为主的旧罗斯世界,而莫斯科以成为蒙古代理人、又背叛蒙古的不光彩形象而崛起,成为罗斯世界的暴发户。
这也意味著罗斯世界被分成两半:依附于蒙古的、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亚洲一半,以及依附于立陶宛的、以其他商业城邦自治形式为核心的欧洲一半(相当于今天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半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、乌克兰的绝大部分)。
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流亡的东罗马公主,让莫斯科得以在政治上继承东罗马帝国的法统,以所谓的「第三罗马」自居。如果它没有继承东罗马的法统,那么莫斯科公国的地位还不如立陶宛大公国,更永远比不上跟法国和德国,然而新引入的拜占庭上层结构则使得莫斯科更加自外于欧洲。俄罗斯最大的痛苦就是永远无法成为欧洲!
■上半身是欧洲人,下半身是斯拉夫人?
西欧派(上层)VS 斯拉夫派(下层)的纠葛与对立
作为妥协而诞生的罗曼诺夫王朝,是经过混乱、分裂后的俄罗斯重新出发、全面追求欧洲化的新时代。俄罗斯跳过波兰,直接从西欧输入技术和思想。从彼得大帝到凯萨琳大帝,俄罗斯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像欧洲人;拿破仑战争以后,俄罗斯的国家威望和利益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。
然而西欧化同时强化了沙皇的专制,圣彼得堡的欧化建立在针对俄罗斯广袤内地的殖民之上。农奴制度的出现,意味著下层的东正教社会与上层的欧化阶级再度分裂。
「十九世纪的俄国自由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人认的祖先是基辅罗斯,他们要把俄罗斯人变成欧洲人。沙皇本人,至少莫斯科的沙皇,认的是拜占庭,他们要做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。而欧亚主义者认的是蒙古帝国。俄罗斯的大一统性并不来自于欧洲,甚至并不来自于拜占庭,而是来自于蒙古帝国。」
这些辩论幽灵般缠住了俄罗斯人的思考。「我到底是俄罗斯人还是欧洲人,还是两者都是」,「俄罗斯是既非欧洲、又非亚洲的一个单独的世界」。这些深层疑问,通过托尔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写作,通过自由派和三位一体专制主义者的冲突,通过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冲突,深刻地撕裂了俄罗斯社会。
■乌克兰的民族发明被苏联冻结在一九一八年,战争之火能够解冻吗?
俄罗斯帝国晚期推行的地方自治实验和陪审制,在宪制意义上是继续「成为欧洲」。在为欧洲式的立宪君主制做准备的同时,也必然产生了一系列民族发明: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乔治亚、乌克兰、白罗斯等。
但是,一战的出现和布尔什维克的成功逆袭,以及列宁式的极权国家出现,把这些正在展开的欧洲式民族国家发明状态一刀斩断。苏联像一个巨大的冰箱一样,把俄罗斯帝国内的各民族冻结在一九一八年。一九九○年代苏联解体后,这些被冻结的民族重新回到一九一八年之前,分别产生自己的民族国家,如白俄罗斯、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。这是普丁政权不愿承认、却没有办法抗拒的历史。
从这个角度看,乌克兰战争是三十年前苏联解体的巨轮、碾过罗斯大地后尚未消失的历史尘埃。而从整个罗斯世界的文明和宪制演变来看,俄罗斯入侵乌克兰,再一次证明莫斯科成为欧洲而不能,逃离亚洲而不得的历史困境。
本书是刘仲敬关于「文明和宪制」的系列讲稿之一,作者的切入角度非常独到,避开了一般常见的传统政治史的写法,比如热衷于描写王朝的兴衰、沙皇等宫廷上层政治人物的故事,而是逆转读者对文明的认知,从地理、社会组织结构、宪制演化的角度解读「罗斯大地」的历史和政治演变。
从文明和宪制的角度看俄罗斯,它是一种次生文明,其历史演化无法摆脱被地理牵制的宿命,而不得不变成灵魂分裂的国家。而莫斯科偏好用专制的形式,来解决其上下层阶级和东西方文化的结构性矛盾,否则就会造成地理的分裂!这种模式,似乎变成了俄罗斯的宿命,成为欧洲而不能,逃离亚洲而不得,在进退维谷中维持一个横跨欧亚的专制帝国的运作,这就是俄罗斯帝国在人类文明史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。
Share